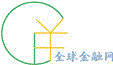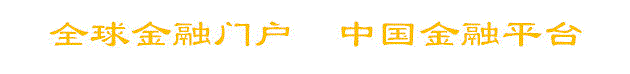由金融时报社主办的“2014首届金融时报年会暨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颁奖盛典”于2014年12月26日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出席并演讲。
陆磊表示,他觉得货币的确是适度的,因为结构性的因素。基础货币仍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因此整个货币条件应该来说是合适的。
实录:
陆磊: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金融时报的首届年会!我也在想,在这样一个隆重的会议当中我讲的主题应该是什么?我当时想了一下,“新常态”肯定是大家讨论的焦点内容,于是我稍微能不能变一变,谈一下在“新常态”过程中,无论政策制定者还有我们金融同业共同关注的不确定性问题。虽然大家都知道“新常态”的若干个解释都已经是既定的,但是无论如何,在未来的过程中,我们仍然要关注很多可能给我们带来运行当中的风险因素,并进而进行有效的不确定性管理,或者风险管理。
围绕这样一个主题,我大概谈三个观点,不见得正确,同时谨代表我个人,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金融行业所面临的整体性风险的预判,应该是结构性压倒总量性,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研究的一点心得体会,供大家参考。为什么这么说呢?无论中外学者在最近这段时间都反映出来,可能全球的增长率面临一定程度的回归。究其原因是生产函数的变化,而生产函数的变化是要素禀赋的变化。中国从资本相对稀缺,技术相对粗放,资源的使用似乎无极限的状态转向劳动力可能出现刘易斯拐点,而资本相对封闭,技术面临创新,资源的消耗面临极限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使得我们不得不寻求某种新的增长形式。
当然,这里面从学术角度出发,我也提出个人的一点看法。我倒是不认为我们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因为创新本身它是要有平台和载体的,技术往往就是创新的一个平台和载体。所以,能不能从学术角度更加准确的理解我们面临的驱动变化呢?我想很可能我们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为什么?因为原来我们更多关注是总需求,而政策是改变总需求,或者说实现需求波动的重要因素。但是,现在出现了供给结构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寻求增长点,增长极,实际上就是从谁来买我的东西转变为我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种困惑将伴随我们很多年,在未来一段时间。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看到在技术层面上具有引领新的一些新的互联网企业的出现的时候,大家会乐此不疲的去追逐。大家也会想,这对供给结构构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这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
在这样本质性问题的冲击下,作为经济和金融的反馈机制够发生变化了,从金融业角度出发,我该从什么来源,什么样的角度获得低成本的资金。与此同时我的资金运用应该配置到哪些场合当中去,这跟以往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考虑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主要考虑规模的运行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我称之为结构性的风险,因为我们面临不确定性。
正因为如此,假设大家同意我刚才所说的观点,于是我的第一个观点的结论是,周期性因素正在被结构性或者趋势性因素所压倒,在重新塑造经济和金融运行的内外环境。
那么,从这样一个结论出发,第二点我们发现规模性的金融资源配置将被结构性的金融资源配置所压倒。也就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将不再是我能做多大的贷款和做多大的全社会融资总量,而是我金融资源能够配多少,在地区上,行业上应该怎么做,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主观点,经济到金融,我们发现结构性因素正在塑造未来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不确定性。
第二、如果这样的结构性因素正在上升,那么在宏观面上我们将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呢?因为刚才我的第一个观点可能是相对中长期的,而大家很关心的可能是2015或者2016这些短期性因素。在这儿我也带给大家一些不成熟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在未来一到两年,“深改+法制”将构成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引领。而这种引领将使得经济和金融,在座的金融行业的同事们,你们都会发现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恰恰201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GDP增长率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这也会在金融行业当中引出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资金来源变了,资金利率结构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往大家可能更多关注优质客户,但是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优质客户结构将会下沉,因为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正在发生可喜和积极的变化。我们金融行业的资产配置是否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呢?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观点,在宏观变化当中,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加开阔一些,放眼全球,应该说两大经济增长极在短期内将是明显形成的。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尽管我们自己跟自己比,我们的增长率可能有所放缓,但是放在全球,我们仍然是最高的增长水平。无论多悲观的估计,2015年或者2016年我们仍然是最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做出很多相应的一些判断。比如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对制造业的塑造会是什么样的,中国对周边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或者引领作用会有多大?同时还需要评估美国,包括它的经济增长,它的就业形势和美联储的相应准入。在这样一种深度融合的经济体制间的交互关系当中,我们将发现我们在2015和2016年可能经济的运行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悲观,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观点,自然而然谈宏观离不开政策,政策当中很重要的是货币政策,很多人说松还是紧,我并不想说这样一个观点,我只想说货币是不是适度的,我觉得货币的确是适度的,因为结构性的因素。比如我们外汇帐款的增长率正在下降,但是与此同时,我们通过SLO,SLF和MLF等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创设,新增的流动性恰恰跟外汇占比的下降之间形成了精准的关系。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基础货币仍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因此整个货币条件应该来说是合适的。
因此,在这样一个宏观环境下,我们能不能得出一点结论呢?结论如下:制度和结构性的角度使得宏观与微观,货币与金融层面上的流动性管理将上升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大家可以观察,是不是我所说的在全球范围出现中美两大经济增长极的重要变化。再与此同时,在货币层面上,流动性管理的重要性正在上升。所以,金融行业也好,政策制定者也好,给整个金融业制造或者营造一个比较好的适度的流动性,这将是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观察到的重要的经济现象。
第三、金融行业的自身的变化是令人瞩目的。这里边同样也是需要提示一下,因为我所谈的是风险,是不确定性。 2015-2016年有哪些不确定性值得我们关注,无非是以下几个看点供同事们参考。 第一、大宗商品价格是不是存在底部以及何时出现底部,因为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在过去一段时间呈现了比较低速波动的态势,整个价格是往下走的,PPI在过去33个月在中国呈现负增长,特别到11月份我们PPI负增长7%,这对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构成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我并不做定量的评估。如果上游价格持续保持低位,很可能下游价格不见得会出现突飞猛进的上升。这使得我们必须在未来一段时间做出相对正确的判断。
第二、信用主体的流动,我相信金融行业一定在判断未来的优质客户在哪里?无非我们所参照的对象是企业、政府和个人。这里面大家也知道,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在2013年6月份是7110个,它的融资占GDP的比重大概30%左右,但是与此同时企业占GDP的比重大概150%左右,此外还有影子银行,根据国外金融委员会的测算,大概同样占30%左右。其实量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中国是间接金融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所以,在评估我们的合理负债的时候,是债务融资占主体,并不是主权融资占主体。所以,它不能单纯的或者简单的进行国际比较。实际上我们要看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不是安全的,是不是稳健的。结论是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经过相应的财务评估,并不能看到上述的主要借款人会出现非常明显的负债问题,仍然是属于优的。难道一点问题也没有吗?我们在关注错配问题,如果搭配不当,一定会出现再融资,而阶段性的再融资会对债券市场,银行信贷和整体金融的流动性都构成相应的冲击。
第三、金融业自身的融资的综合成本与实体经济部门的筹资成本之间面临一定的关联性。这一点我们往往在理论分析和政策分析当中是割裂的。一方面我们看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难,成本高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大量的银行的经营结构表外筹资的成本也相对较高。所以,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资金来源成本相对比较高,你资金运用的价格就下不去。所以,这需要政策当局和我们在座的金融行业共同想办法做一些创新,使得我们社会整体的筹资成本能够达到稳健的为各方所接受的状态。这是第三个问题,我相信在2015年我们也将观察到相应的政策摆布,政策调整和金融行业层出不穷的新产品和新服务。
最后,作为一个第三点的结论,如果我刚才的一些总结,不确定性可能是粗浅的,不见得完备,可能还有其他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上述我所提到的三个问题,那么金融行业该怎么办呢?我想还是两性,要有弹性,要有韧性,有韧性就意味着自己能活。在各种各样的冲击面前不至于惊慌无措,或者不至于出现大的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有弹性就意味着面对这些环境还能找到真实的优质客户,并进而能够获得适度的盈利。因为我们在座的金融机构基本上以盈利为自身存在的基本目标。
所以,一句话做一个总结,根据我刚才所谈到的整体性风险可能是结构性的,宏观面既要考虑国内和国际,同时还要考虑货币条件。在微观面,我们重要的一个思考方向是筹资成本和我们的资金投放的价格。那么,综合上述,一个结论是风险是任何一个新兴经济体在走向成熟所必须要面对的。而政策当局是必须要对相应的分析进行宏观面的考虑,而金融行业也是必须要针对这些不确定性来做。我相信我们走过几轮经济周期之后,我们应对这些问题的能力会更加提高,我们的工具会更加充分。所以,最后的宏观经济基本稳定,这些效果会变得更加好!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