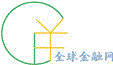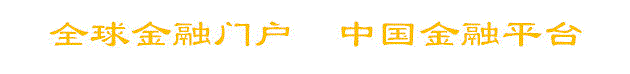|
2015年11月4-5日,由凤凰网与凤凰卫视联合举办的“2015凤凰财经峰会”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李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在此应邀参加这个会,刚刚主持人说互联网,说的不是互联网,说的是降低杠杆。大家知道,本轮危机就是一次债务危机,高杠杆是构成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此去杠杆就是降低杠杆率构成当前世界经济恢复的必要环节。去杠杆化已经七年了,但是数据显示,这个情况并不理想,世界各国的杠杆率都在普遍提高。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杠杆率的提高有在全世界蔓延之势,有研究显示,如果2008年之前全球的杠杆率提高归因于发达国家的话,在那之后,特别是当下杠杆率提高将归因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此不可不查。我们确实查了,所以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在我们党的文件中也是首次。这样一个战略任务是需要完成的,而且是很艰巨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需要做一些研究来刻划一下到底我们的杠杆率状况如何,我们最近这几年完成了一项研究,就是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
从2012年开始,新组建的国家金融智库,就是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致力于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已经有两本了,2013年编制了2013年之前十年的,2015把数据追溯到2014,我们现在有到2014年底的债务情况。债务问题不能就债务问题来研究,因为借钱总是有用处的,所以必须密切结合债务极其密切关联的资产状况来加以判断,这样的话一个完善的资产负债表是判断债务状况、杠杆率状况恰当的框架,也正是于这样一个框架才能探寻合适的去杠杆化的战略和方针。
中国在危机以来,整个国家的负债率在上升,国家作为一个整体,2007—2013年,国家负债率由41.8%提高到49%,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在我们分析的时间区段里,有三个年份是超过了平均水平,就是2009、2012、2013,密切结合这三年中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国家的负债率上升与全球危机的蔓延以及国内经济下行密切相关。刚刚是把国家作为一个总体来看,现在把构成国家的主要部门分别进行分析,2008—2014年这样一个时间段里,各个部门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分别是:居民由18.2%提高到36%,上升了17.8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从98%提高到123.1%,上升了25.1个百分点。金融部门从27.6%下降到18.4%,下降了9.2个百分点。政府部门从40.6%提高到58%,上升了17.4个百分点。2014年末,中国经济整体债务总额为150.03万亿,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70%上升到235.7%,6年上升了65.7个百分点。金融部门又形成负债又形成资产的活动,把它剔除的话,中国实体部门债务规模为138.33万,占GDP的比重从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6年上升了60.3个百分点,上升速度是相当快的。
看到债务之后必须转到另一面去,就是资产,债务上升很快,资产的状况怎么样?资产上升速度比债务增加的速度要快,中国各个部门的债务大都会相应形成一些资产,因此中国作为整体各个部门的资产规模也是相当大的。我们给了两个口径,一个是宽口径,能算得都算上,一个窄口径,只算那些有流动性的,流动性强的资产。宽口径主权资产227.3万亿,主权负债124万亿,资产净值103.3万亿,超过一年GDP的规模。我刚刚说的资产里面,比如有很多土地,繁荣的时候是可以买掉的,如果经济下滑是卖不掉的,土地即便是帐上有,但是不能够现实的形成可以处置的资产,必须扣除。还有大量的国有和事业单位的房地产,也是不容易处置的,所以在考察一个国家真正应对债务能力时必须把它剔除,我们做了这个剔除,得到的最终结论是:中国的主权资产由227.3万亿减产到152.5万亿,窄口径的主权资产净值为28.5万亿,大概是GDP的一半。从资产构成来说,净值中第一是储备,第二是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都是流动性非常高的资产。
根据这样一些数据就会有结论,结论是: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是极小的,因为即便发生了一些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有足够的资产去覆盖它。进一步深入分析的话,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最近几年受人瞩目,而且炒得很热。我们的研究显示,地方政府固然有债务,但同时也有资产,而且还有相当大的资产。到2014年末地方政府总资产108.2万亿,总负债30.28万亿,净资产77.92万亿,总量上讲,后面还有严重的期限错配问题。给大家一个定心丸的同时必须要居安思危,我们研究了潜在的债务,其中最主要是两块,一块是养老金缺口,再一块是银行的显性和隐性的不良资产,这些是或有负债,我们力求使或有负债不要变成实有负债,全球经济进一步下行,中国经济进一步下行,可能会使一些潜在的债务变成实有债务,所以中国主权净资产的增长动态有可能逆转。
(图)这个图刻画了2000—2014年我们的主权资产负债以及政府净值的变化情况,这是总量的,是宽口径的,资产和负债在同时平滑的增长。这个图刻画的是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变化,中国要研究各个部门的行为的话,中国居民在过去一向是不借钱的,在很长时间中国居民负债是很低的。但是随着我们积极鼓励居民消费,随着住房市场化的推展,随着各种各样鼓励消费措施的推出,贷款买房、贷款买车、贷款消费,这些措施的推出使我们看到居民杠杆率稳步上升,现在还在一个很安全的范围内,但是如果再继续发展的话,还是需要控制的。大家都知道美国这次危机首先就是居民杠杆率太高,中国远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图),这是中国非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这次危机之前中国的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是非常平稳的,2009年开始跳跃性的增长。回头看数据,中国的金融数据都是在2008、2009年之后剧烈恶化的,这也说明中国作为全球化经济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部分,我们的经济增长,经济的波动是和全球经济高度一致的。
在研究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问题时,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居民非金融企业、金融企业、政府这四个部门在美国肯定是居民和政府问题最大,在中国是企业问题最大,非金融企业问题最大,所以我们比较细的分析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几个率:一个是资产负债率,07年54%上升到2014年的60%,上升了5个百分点,这个状况居世界的中游,远高于美国、英国的水平,大概和日本、德国比较接近。中国负债占GDP比重2007年是195%,2014是317%,上升了122个百分点。我们这些年来信贷的扩张相当部分就进入了非金融企业,相当部分也进入了国有企业。总和算下来的杠杆率,2008年98%,2014年149.1%,猛增了51%,非常高。如果扣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因为在统计上可以把地方融资平台算为企业,因为它有资产、有负债,把这个扣掉,杠杆率提高到123.1%,上升25个百分点,依然在世界上比较高。我们做的国际比较显示,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在所比较的国家中最高,隐含的风险值得关注。因为在中国企业出问题马上就是银行出问题,银行出问题马上就是财政出问题,财政出问题立刻就是整体经济出问题,中国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传导的链条。所以企业的债务问题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还有一些副产品,有两隔壁李,在国有企业的资产在全部非金融企业的资产占比是稳步而且比较快的下降,这个数据其实对于一段时间里流传的所谓国进民退是不相融的,从资产上来说是国退民进。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在所有的企业中发现工业企业占比下降,就是说服务业的企业资产占比在迅速提高,这两个变化我们认为都是良性变化,第一个变化表明非国企的比重在上升,第二个表明中国服务业比重在上升。
政府部门杠杆率稳步上升,这很正常,而且是国际规律,财政学上有一个定律,就是政府部门不断扩大定律,扩大到不可持续时来一次革命性变化,然后再从一个新的基础上再延续这样一个变化,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对政府提的要求越来越多,当政府不可能通过税收和其他正常的收入途径来为这些要求筹资时,只能诉诸债务,这是很普遍的,我作为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人员,我们已经感觉到中国这样一种状况其实已经开始了。
几个部门分别看起来之后有了一个总图,中国全社会的杠杆率变化,1996—2014,这是我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图有这样一个好处,可以非常直观的告诉我们,从1996年算起到现在,中国全社会杠杆率发生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96年开始到2002是上升的,第二个阶段从03年开始到2008,是平的,是没有上升的。第三个阶段,危机以后继续上升。如果对应这个时期的经济变化,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增长最快的是危机之前的那十年,就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到危机发生那几年是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在10%以上,所谓杠杆率、债务率无非是分子对分母的比率,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大大的扩大了分母,促进了分母的增长速度,所以使得任何债务都不显化,才会有中间这段时间比较平的结果。
为了使这个结果更具科学性,我们做了一个比较,麦肯锡也做了一个,媒体广为流转,广为引用,我们和麦肯锡的方法有一个比较。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基本没有太多的变化,差别主要是在金融部门,金融部门对两个帐户的处理,一个帐户是在中央银行的统计表里面有,叫做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里面两个帐户,一个是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权,一个是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债权,他们统计在内,我们没有统计在内,就是同业往来。大家都知道,同业往来对实体经济其实是不产生多少作用的,同业往来是最后嘎嚓才会起到一些作用,同业往来这几年中国在金融部门涨的特别快,同业往来增长很快恰恰说明了实体经济没有对金融的需求。所谓贷款难、贷款贵,其实大量的资金就在金融部门之间转来转去,大家转那个差。结合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理解,我们认为这样一些东西只是金融交易,而且它会在一个合并报表中负债和负债会嘎嚓,在只剩下很小的数字的情况下,统计杠杆率的时候是可以忽略的,这也符合国际惯例。我们把这样一个情况和媒体广为引用的麦肯锡方法做一个比较,我们认为他们的方法是有问题的。
下面讲去杠杆和资产负债表的风险管理,其他杠杆率在提高,而且中央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刚刚闭幕的五中全会上就提出要降低杠杆率。今后是我们整个金融界乃至经济界的一个战略性任务。有怎样的方法?前面已经讲了杠杆是分子对分母的关系,我们知道分子里有哪些东西,分母里有哪些东西,于是我们就可以很形象的说分母对策、分子对策,我们对分子中的那些因素怎么调整,对分母中的因素怎么调整,无非如此,这样的话大家看得很清楚。分母对策有三:一是还债。或者是资产负债表有资产,有负债,卖资产还债,这是正道,而且我们今后会在相当程度上靠这个。这次五中全会一个亮点,我们前面谈到养老金缺口时明确说用国有资产去填补养老金缺口,这是转移问题,这里也是这个。我可以卖资产还债,但是现在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可能会导致在这次危机中比较通行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卖资产,一个是在情况不好时,资产卖不出价钱,而且卖的是好资产,可能会加速整个经济下滑的过程,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举一个卖资产还债的例子,比如汇率在波动,我们觉得向下行是不好的,于是就卖美元买人民币,把汇率给调上来。这个政策举措如果从汇率操作、国际经济学角度来说很正常,但是从资产负债表架构分析来说就是用好资产换坏资产,我们在整个宏观调控中增加一个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架构的话,就会对现有的很多政策要重新考量。
第二个措施是债务减记。可行性是存疑的,只要有减记发生,就会有负的溢出效应,大家觉得可以赖帐,可以不算数,可以谈判之后减记了,对整个社会信用制度的冲击是非常剧烈的。
第三个措施是交给政府,交给央行,市场操作就是政府去买,央行去买,这次美国危机一开始就是央行去买不良资产,买着发现不对劲,买了之后打水飘,开始买产生有毒资产的企业的股权,这下买对了,等到他的股权价格上来之后再抛掉,当局是这么减的。这应当说也是正道,但是这些政策我们必须瞻前顾后,就是说现在买,今后一定要卖,你现在花了钱今后一定要为这笔钱来筹资,所以有一个跨期的调整问题,你必须要考虑到。举例说,现在美国量宽退出,迟疑、犹豫,进一步退两步,进两步退一步,是因为当年为了把经济稳定住,花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多东西,好不容易稳住了,现在要把它吐出来,卖哪个哪个跌,卖什么那个部门就会受到影响,危机的恢复,后面这个阶段也许可能更复杂。政府买也一样,政府没钱,所谓“李嘉图等价”,别看现在搞得欢,以后还要拉清单,未来税收负担会加重,将来会产生债务,也不是太好的政策,但是可以暂时止住。
下面看一下分母,所谓分母对策就是增加GDP,说白了就是增加GDP,具体路径是积极推动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提高经济效力,它不立竿见影,但却是治本之道。希腊搞来搞去不愿意接受那个方案,全民公决,到最后和债务人谈,最后还是这个结果,希腊要用改革换救助。你只要认真想问题,认真想一想所有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展经济,所以改革并以此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长速度,同时控制债务增长速度,依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谈到“十三五”的经济增长速度时非常恳切地说,发展还是硬道理,因为我们所有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
还有一种去杠杆的办法,杠杆转移,其实不是总体去杠杆,刚刚说企业杠杆很高,能不能通过一些方法把企业杠杆率降下来,让别的部门去承接,是可以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种统一的政治体制下,是可行的,在西方大部分发达国家是不可行的,我们这儿是可行的。通过这个办法把一部分企业的债务变成银行债务可不可以?肯定可以。把一部分这样企业的债务变成另外一些企业的债务可不可以?通过债转股把债务变成股份可不可以?也都可以。所以在中国存在着所谓杠杆转移这样一种去杠杆化的办法。不管怎么说,这是中国的优势,这样帐户处理也比较简单。杠杆转移是解决我国地方政府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问题的现实途径之一。
前面讲的都是宏观的,现在看看结构,很多问题深藏在结构之中,有三个结构值得我们关注:
1.期限错配。期限错配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债务中。前面说地方政府有很多的资产,凡是熟悉中国经济的都知道,地方政府富可敌国,有很多东西,相对资产来说,负债是比较小的,一百零几万亿的资产,不到三十万亿的负债,是足可以弥补的。但问题是地方政府手头掌握的负债是短期的,而他的资产是长期的,于是就出现了金融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期限错配问题。对于这样一些问题必须综合施策我们列了三个对策,建立稳定有效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今后中国投融资机制的问题主要是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机制问题。因为地方政府也不是想随便就负债,负债是想改善我们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一搞20年才能回收,甚至不能回收,怎么办?针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机制,是中国下一步金融改革的攻坚点。
2.大力发展长期信用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正处在传统工业化已经结束,新兴工业化正在兴起,要钱,而且要长期的钱,中国的城市化正在过程之中,不管怎么算对城市化有的这样算,有得那样,我觉得没有那么多潜力,但不管怎么样会是中国一段时间内很大的事,城市化要投资,也还是要长期资本。中国不缺短期资本,就缺长期资本,所以长期信用类的机构,而且因为大量涉及到基础设施,特别是基础设施,它的投融资机制问题,政策性特点的问题我们必须照顾到。
3.依据收入和支出,责任匹配的原则,积极调整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我们知道城市化、工业化的压力都在城市,但是钱在中央,如何使这样一个钱的来源和钱的使用不匹配的关系,必须调整支出责任和收入的匹配关系,收入中央和地方政府是各一半,支出地方80%,中央20%,有30%都是各种各样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中有很多问题,最近这几年一直在调整转移支付的格局,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重新划定收入和支出责任,这是现在一个很重要的改革的方面。
资本结构的错配,主要体现在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里。中国的金融结构是间接融资为主,意味着我们提供的资金到了资金使用者手里,大多数只能形成债务,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本身就有提高杠杆率的倾向。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改变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重申了这样一个目标。
两个对策:一是推动中国金融结构从债务性融资为主向股权融资为主的格局转变。二是必须认真考虑在过去规定中国的银行是不许投资的,但银行又掌握了最大的资金,资金出去不许投资都市债务,可不可以借鉴欧洲、日本、德国很多国家的经验,让银行有一些投资权,这些问题也都在研究之中。
再就是货币和资产错配。通过编制国家资产负债,我们发现中国对外是处在一个很有利的地位上,所谓国际投资头寸的地位是正的,世界上是正的很少,中国是一个,日本是一个,负的很多,大量的欧洲国家,美国都是负的。这是存量的问题,每个国家既对外有资产同时又有负债,我们要算一个总帐,这样一个资产负债的结构收益如何,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对外的投资头寸是正的,但是我们收益是负的,美国对外投资头寸是负的,但收益是正的,就发现了资产负债的严重不匹配。美国的情况是对外负债都是美元,当然有他特殊的地位,美元利息才多少,零,他对外的资产虽然规模没有负债大,但是都持有被投资东道国的股权类资产,也就是说通过他的投资可以充分地享受被投资国家经济增长的利益。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企业收益率都高,我们持有一点美国的债权收益率都低,这就是差别。当然这种状况也是长期形成的,与美元长期是国际货币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必须从现在认识到这个问题,开始调整,我们认为这个调整还会有相当长的时间。在负债链要争取增加人民币负债,减少外币负债,要争取人民币负债,先要人民币走出去,于是人民币国际化就构成管理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的必要条件。
两个星期前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英国送了一个大礼,在伦敦城发了一笔以人民币定值的债权,就是我们到外面借人民币债务,人民币是我自己印的钱,那个债务负担其实是很小的。但是这个或者还要很漫长,所以我们要通过“一带一路”战略,自贸区建设,增加人民币在我国对外负债中的比重,逐步降低我国的对外负债成本,我们的成本是很高的。然后是资产方大有可为,扩大内需,减少对外需依赖,放缓外币定值资产积累,就是储备减少,从我们资产负债表分析的角度来说,因为储备收入太低了,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持有,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因为国债的收益率就是零点几,这种情况肯定是要杜绝的。所以我们要通过大量的对外投资,而且是增加对东道国的企业股权的持有,这样才会大规模提高我们对外的收益率,从而扭转资产负债表中货币和资产错配的问题。这显然也不是三天两天能做的事,但是今天要认识到,实施这样一个扭转战略。
总之,中国的党中央提出了要岗地杠杆率的战略目标,确实是问题所在,要想真正落实这样的目标,我们必须在资产负债表的框架下对我们的资产负债逐步有一个清晰的、科学的、系统化的了解,我们的研究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
欢迎关注全球金融网微信公众平台
|